来源:世界名人书画网 2020-12-30 15:12:09
杨汉立,作家,诗人,《侗族时光》作者。
杨仕芳,小说家,《柳韵》《风雨桥》杂志副主编。
时间:2020年12月19日;方式:线上。
杨汉立侗文化系列散文集《侗族时光》列入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重点作品出版扶持项目,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部散文作品集由22篇侗文化散文组成,计21.4万字,每篇相互关联,形成系列,合为整体,却又独立成篇。这部散文集最先在《风雨桥》杂志连载三年,后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发展工程2017年度出版扶持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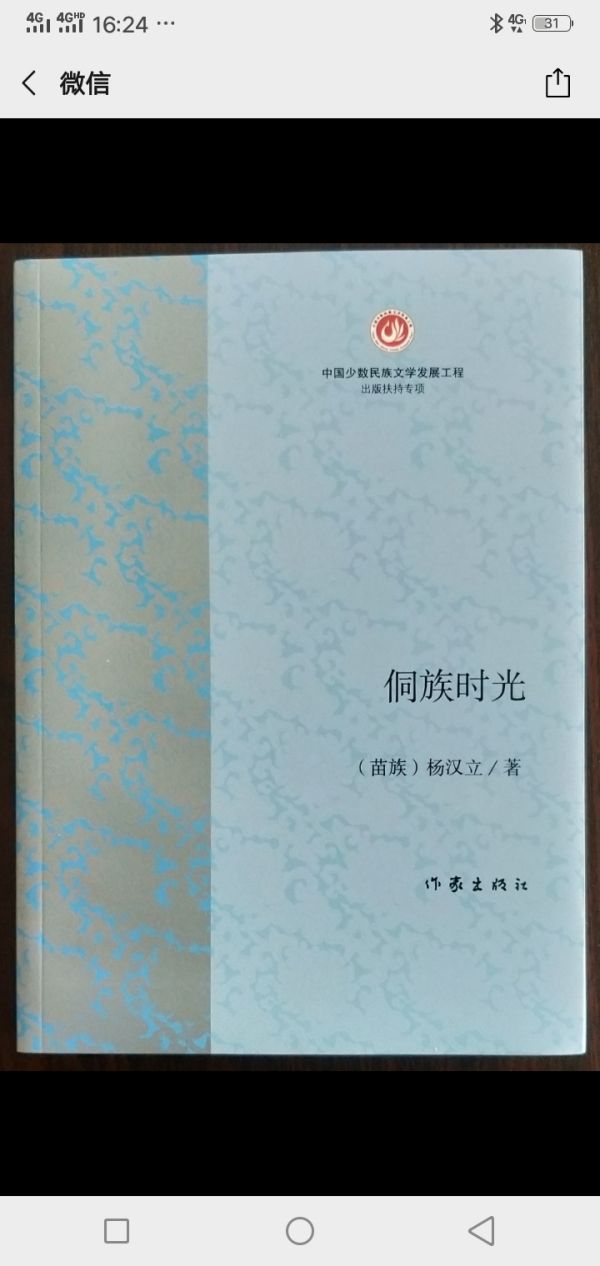
作者长期生活在湘黔桂边界的侗族地区,既是一名作家,又是一名文化学者,长期研究古代文化和湘黔桂边界地域文化,有多部文学作品、学术文章结集出版。本部作品以散文的形式为世人解读不太为外人所熟知的侗族世界,全面展示其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奇异风俗、经济发展的斑斓色彩和独特魅力。作品既有文化深度,又有优美的语言,还有丰富的内容和有趣的故事,文化品位、文学性和可读性兼优。
广西著名侗族作家杨仕芳与《侗族时光》作者杨汉立在线下进行了对话。
1.杨仕芳:杨好,恭喜新书《侗族时光》出版。于侗族文化和文学来说这是件喜事,它的意义是多重的,不仅以散文形式展现侗族文化,还是一个苗族作家眼中的侗族。谈谈你对这本书做了什么准备,又遇到什么困惑?
杨汉立:本家,您好。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以文学来展现侗族,以前有不少作家做了大量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多成就,您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您的小说都切入了侗族底层的痛楚。但是,系统地展现侗文化还有很多空间,这必然需要更多的作家为之付出。《侗族时光》可以算是我对侗族文化和文学以及侗族地区的一种报答。
我虽然是一个苗族作家,但是我生活在湘西南侗、苗、汉杂居地区,我的家族和家庭都是侗苗融合在一起的。其实,自古以来,侗苗一家亲,文化具有诸多的相似性。我作为一个苗族作家,可能有一些“旁观者清”的优势吧。
要说对《侗族时光》的准备,其实自我一出生就开始准备了。别笑,确实侗文化让我自小就受到了滋养,比如那些习俗至今还历历在目。当我上完学走向社会之后,我零碎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地域文化,对其中的侗族文化很有兴趣,后来多次参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侗族文学分会的一些研讨会和广西三江主办的“文学与地域”研讨会,也曾经被选为侗族文学分会的副秘书长,因此我就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观察侗人的生活,阅读侗族有关的著作,对侗文化进行自己的思考,对侗文化也有了空前的热爱,总有一些想展现它的冲动。
所以,这本书的孕育和出生,还需要感谢侗族,感谢侗族文学学会,感谢三江,感谢《风雨桥》,感谢中国作协和湖南省作协。
可是,我作为一个侗文化的草根研究者,有诸多的不便,手上并没有系统的资料,更不用说受到专业的训练,几乎所有采风和研究的费用都靠自己解决;作为生长于汉化严重的侗苗地区的一名作家,也无法有当代侗族核心地区侗人那种更真切的生活体验和情感积淀;在当代,一方面时代必须往前走,侗人也必须过上现代化的生活,而古老的侗文化面临着被现代文明同化的危机,对于这一切我只能心里着急,不断呼吁保护,又乞求侗人能把日子过得更好些,对于如何反映两种文化的冲突,却感到一直找不到切入口,更难找到恰当的答案。这种困惑时时阻碍着我的写作。
2. 杨仕芳:现在回想起来,这本书的出现有些偶然。最初是我向杨约稿,在《风雨桥》上开设专栏:“一个人和侗族”,这是《风雨桥》的尝试,事实证明,这个尝试是成功的。我想问杨的是,你是一位苗族作家,是什么原因让你答应为这个专栏写稿?
3.杨汉立:偶然中有必然。本家您想到开“一个人和侗族”专栏,是因为您一直尝试从更多的视角来审视和表现侗文化,从您的小说看,其实是站在普世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侗民族的。而我之所有毫不犹豫地答应,如前所说,侗苗文化是我的生长土壤和长期的聚焦点,当然我也更多地站在现代视角来看待侗文化。这正所谓一切发生的事就是最好的安排。同时,我一直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让我要为保护民族文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而我所能做的,仅仅是用我笨拙的、软弱的笔来抒发我内心这种固执的情感。由此可见,开这个专栏并坚持三年也并非偶然的。
3.杨仕芳你的身份是苗族,应该说你以苗族作家的身份和目光来审视和书写侗族,不知在这里写“旁观者清”来形容是否恰当,每个人总是会受某种族群的心理暗示,我想你在下笔时会有别于侗族作家的感受吧,可否谈谈?
杨汉立:其实,一切都是相对的,所谓 “旁观者清”也是。作为一个苗族作家能看到侗族的与众不同,至少与自己民族不一样的特点,比如被称为“侗族三宝”的鼓楼、大歌和风雨桥,苗族有没有类似的东西,有啊,但侗族的格外突出、格外耀眼,而且其他民族没有。这种物质文化,蕴含着深厚的非物质文化,其内涵太深厚了,可以穿越时空,一路溯江而上,欣赏沿途风景,一直抵达民族的历史源头。同时,如前所言,侗苗一家,在当我审视侗族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时,会把对苗族历史、当下和将来的思索融入到一起,这样产生的内心冲击更大。与侗族作家相比,对侗文化的理解,我会有诸多不及的地方,但可能也就有侗族作家所不及的超脱,更能跳出侗族看侗族。
4.杨仕芳:从你的角度如何看待侗族文化和苗族文化,无论是哲学、宗教、信仰等都有其自身的特点,那么在你看来,这两者间最大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
杨汉立:这个问题问得十分深刻,让我有些难以准确表达。侗苗文化十分接近,都崇拜自然,信奉万物有灵,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乐观通达,热情大方,喜歌好舞。你看,侗苗古歌中的民族诞生于树木、动物之类的传说,侗族的合拢宴和合款制度,苗族的理贾制度,就是这方面的体现。侗苗民族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在逼仄的空间生生不息。自远古起,侗苗就是在朝廷的不断征剿中,且战且迁徙,两个民族迁徙的主体线路都是从黄河中下游一直迁徙到现在的西南区域。只不过是侗族迁徙路途更遥远,更复杂,而苗族还曾经建立过强大的古三苗国,后来的楚国也是苗族建立起来的。
因此,为了生存,侗族更容易与其他民族达成和解,特别愿意最大限度地接受封建王朝的改造。所以,侗族表现出“水”的特性和“月光”的特性,被称为“依山傍水而居的民族”和“月光民族”。我想不仅是指其居住和婚恋的表象,更是道出其民族的柔性、融合性、包容性的本质特征。而苗族,可能因为曾经强盛过,相对来说更刚强些。
5.杨仕芳:谈谈你对当下文化散文存在和发展的看法,以及你今后写作有什么计划。
杨汉立:把文学分得这么细是现代人搞的名堂,古代没有这么分类或者说。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专门深入地研究某一类别的文学。把文化散文作为一种现象来研究,也是可以的。文化散文曾经高热,近些年受到了冷遇甚至指责,我认为棒和骂都是不正确、不公平的,应当心平气和地对待。只要文学还在,文化散文永远有一席之地。
文化散文以往不少作品表现为事物大海上的浮光掠影,对事物积淀的文化研究不够、体验不深,只是堆积了一些蜻蜓点水式的文字或卖弄了一些资料,或者为自己武断的结论罗列了一些所谓的证据。以我十分有限的阅读,也欣喜地见到一些作家对文化散文作了不少探索,我在《民族文学》《十月》《散文》《湖南文学》等杂志看到了不少沉浸到某些事物的文化组织结构中,发酵出文化的醇香。《风雨桥》在这方面一直努力掘进,坚持开辟文化散文类的专栏,为文化散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一个人和侗族”专栏坚持了三年,实属不易,其功颇大。
事物总是曲折前进的,较以前之过热,当下的文化散文步入了一个相对正常的轨道。我偏居一隅,与一井底之蛙无异,对于文化散文发展的看法就像对于文学发展的看法一样,我是迷糊的。但是,我始终认为大道至简、万物一律。无论文化散文,还是其他散文,抑或是小说、诗歌,必然从熟知事物开始,高度与事物融合,实现物我合一,或者说物相和意相水乳交融,能够看到事物内部的肌理和温度,以及事物深处的黑暗与从事物深处发出的光亮,作为作家,就要用恰当的文字去描绘这些,并浸染自己情感,可能更多的是要跳出某个事物、某个区域、某个民族,来看待它们,这应当是文学和作家的使命。文化散文不光要让我们走回过去的时光,还要帮我们剖开文化的内核,记录不同文化的冲突。比如,当下需要记录现代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爆破式推进时,传统文化与全球化文化冲突中,传统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什么痛,要怎么走?这一系列问题,是文化散文需要去记录和回答的。这应当是文化散文重任和出彩的地方。
再次感谢仕芳的关心。由于我才疏学浅,这些一孔之见不一定正确,希望大家不要被我误导。好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我几斤几两,也会原谅我的无知。(文/图 杨仕芳)